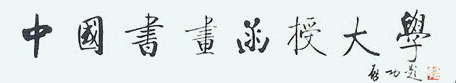无手画痴的爱情变奏曲
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无手人”王振东和妻子王素平就在西单地铁站的通道里露面了。
他没有双手,仅用两只长短不一的胳膊夹着画笔画出一幅幅豪气逼真的国画吸引了许多的国内外游客的注意力,人们驻足欣赏、购买。他神情专注地埋头画画,以满足游人的选购,妻子在一旁给游人们讲解着每幅画的意境和绘画技巧。
妻子娴熟内行的讲解使更多的人不仅对画产生了兴趣,更对他们这对患难夫妻产生了敬意。
两个小时过去了,王振东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停下手里的活,直起身子喘着粗气。这时,王素平连忙扶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喷枪”,一边朝他口里喷洒着药液一边向游客们深表歉意地说:“对不起!他的哮喘病犯了,请大家原谅,他今天已经超过两个小时了,不能再画了。”接着,她迅速地收拾完东西往袋子里一装,推着自行车驮着王振东在游客们遗憾的目光下向他们住的地方走去。
对王振东来说,这是第二次闯京城了。12年前,他是带着身心俱伤而来又带着满腔遗憾离去的。这一次,他是在经历了爱情的变奏之后带着希望和梦想而来。
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王振东,望着妻子的背影,想到这么多年来,他在爱情上的坎坷经历,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手没了,爱情落荒而逃
1967年11月亮19日,王振东出生在河北省徐水县漕河镇中索营村。厄运降到他身边的时候是1990年底。
那天,他往往常一样按时到镇办的鞭炮厂里上班。上午10点多钟,他正聚精会神地插着鞭引时,忽然“轰”的一声巨响,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手里的五十万响大鞭引爆了……
顿时,血肉模糊了他的意识,他渐渐失去了知觉。
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县医院里一个星期了。
“爸,爸……”这是他醒来后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不满两岁的儿子在吐词不清地叫着他。
“妈妈呢?”王振东用眼睛扫视了整个病房没发现妻子,下意识地伸手去抚摸儿子的头。他感觉伸出去的手有点异常,定睛一看,差一点晕了过去:他原本灵巧的一双手却齐刷刷地没了!
他慌了,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着:“我的手!你们把我的手弄到哪儿去了?没有手,我以后怎么生活呀!”他望着两只光秃秃的胳膊,号啕着。
医生来了,从他们支支吾吾的言谈中,他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他被送到医院以后,妻子见他双手已被炸掉,断定他将来会丧失自理能力。她不愿意这样伺候一个残疾人一辈子,丢下儿子,和一个外地老板走了。
王振东听到这个消息后反而镇定了,他激动的情绪渐渐平缓下来。
他不再喊叫,也不再号啕。他咬着牙,用缠满绷带的胳膊将儿子揽在怀里,喃喃自语:“儿子,妈妈不要咱们了,爸爸虽然残疾了,但绝不会抛弃你,爸今后就是要饭也要带着你一起要。”
父子俩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1991年春节过后,王振东茫然失措地走出了医院。妻子走了,这个家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含义,成了一个被掏空的了躯壳。
王振东出院后,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带着儿子在哥哥家里住了一个多月。他实在呆不下去了,一个大男人整天靠着别人养活,那滋味该是何等尴尬。
为了生存,也为了今后孩子能读上书,无奈之下,他背着儿子和一床棉絮走上了乞讨之路。一周后,他们来到北京。
北京也并非王振东想象的那样是“闯天下”人的天堂。当他肩驮儿子、臂携包袱一路乞讨来到北京时,他才感到作为一个残疾人要在北京生存下去比在家乡更加艰难。
从离开家的那天起,王振东就抱定了这样的想法:既然出来了,就一定要闯出个名堂来。吃苦对他来说已不算什么新鲜事了。
每当最后一线光亮被黑夜淹没的时候,王振东就背起儿子在天桥下或地铁的通道里与那些丐帮和流浪汉们争一方栖身之处,争不赢就只好露宿街头。秋凉以后,怕儿子露宿着凉,王振东就把儿子放在自己的肚子上睡,他的肚子成了儿子的温床。东方射出第一缕阳光时,他又带着儿子出来乞讨。
冬天是乞讨者最难熬的日子。
北京正刮着刺骨的寒风,下午,王振东父子来到复兴门桥下避风。一个老奶奶发现冷得缩成一团的儿子又脏又饿,就心疼地对王振东说:“这么冷的天气,孩子又冷又饿怎么受得了?这样吧,我家就在前面不远,我带他去吃点饭。”
老奶奶见王振东有点犹豫,就开门见山地说:“你放心,孩子丢不了!”
看着老奶奶满脸的善意,在确信她不像一人拐卖儿童的坏人时,王振东答应她把儿子带走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了,站在原地傻等的王振东突然有种不详的预兆。他把随身带来的破棉絮放在桥下,急忙沿着刚才老奶奶领走儿子的方向寻去,寻遍了整个胡同,也没见老奶奶和儿子的踪影。
两个小时又过去了,已经到了傍晚。王振东一下了懵了,这才意识到儿子被人骗走了。
王振东垂头丧气地朝回走,他一边走一边想:这下算完了,儿子丢了,唯一的牵挂也没有了,这么大个人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呢?他觉得自己被人骗得太惨了,感到没脸见人,想一死了之。
但他还是不死心,他想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看一眼,恐怕老奶奶把儿子送回来了呢。尽管他自己也感觉这种想法太天真也太幼稚,但那毕竟也是一种可能呀,恐怕呢!
他带着一线侥幸的希望,腿像灌了铅似地慢慢朝回挪动。
远远地,他忽然发现放行李的地方站着一个孩子。王振东不敢相信地揉了揉急得昏花了的眼睛,仔细地瞧了瞧:不错,那确实是自己的儿子!
他急不可奈地奔了过去。只见儿子的旁边还多了一个包袱,里面是崭新的孩子衣服,有单的也有棉的,还有一些吃的东西。他一把将儿子紧紧地揽在怀里,泣不成声。
从儿子断断续续地叙述中,王振东才知道:原来,老奶奶领着儿子吃完饭后,又带他去洗了澡,洗完澡又领他到商场买衣服和食物,等他们回来时,已经不见王振东了,老奶奶断定他去找儿子了,就留下了儿子和买的东西走了。
王振东万分感激:这么好的人,他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能说上,而且连姓名也不知道,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恩人呢?王振东只好把这份感激埋在心里,用另一种形式去报答。这一夜,他搂着儿子甜甜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像刚刚做了一场梦,老奶奶给儿子买的一大包衣服和食物不翼而飞了,就连他白天乞讨来的十几元零钱也像蒸汽一样被蒸发了,不知去向。
这世道也太不公平了,黄鼠狼尽拣病鸡咬!王振东在喟叹这些人“挖眼睛不怕眼睛瞎”时,也只好认命了。
命运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就在王振东的心情极度颓废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让他得到了精神上的鼓舞。
他沮丧地在一家大超市前闲逛,突然被那个大彩屏上播放的一个人物专访吸引住了。专访的人物是当今著名的口足画家刘京生大师,大师双臂高位截肢,全靠脸和肩夹着笔作画,成为世界上知名的口足画家。
专访已经播放完了,他能够顽强地作画成为一代大师,我以前在学校读书时就喜欢画画,而且基础一直不错,我为什么不能重操旧业,拜大师为师作画呢?
想到这里,他浑身来了劲,胆量也大了起来。他按照电视上提供的线索径直找到市残联。
在刘京生的办公室,大师热情地接待了他,也很同情他的遭遇。当王振东怯怯地提出想拜大师为师时,刘京生爽快的说:“好吧,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
临走时,刘京生语重心长地开导王振东说:“这人啦,要想出人头地比别人强,就要比别人多付出,其它没有捷径可走。”
从此以后,王振东便以“无手人”为艺名边乞讨边画画,经刘京生从理论和技巧上的指点,他的画进步很快。但是,在北京这样一个艺人云集的地方,他的画显然是无人问津的。为了谋生,他不得不遗憾地离开京城,另谋生路。
肢截了,爱情翩翩而来
王振东早听说广州是经济发展的前沿。他想,在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艺术也会一定会倍青睐。
1994年底,王振东带着儿子开始闯荡广州了。在失去了爱情的日子里,他把所有的家都倾注在画画和儿子身上,这是他爱的全部。
王振东来到广州后,就和儿子一起在大街上画画,儿子当他的助手。
广州这地方确实充满着金钱的诱惑力,虽然起初买他画的人并不多,他也知道,买他画的人并不是真正喜欢这些画,而是出于同情伸出援助之手。但每天也能收入好几十块钱,比在北京乞讨的日子要好过多了。
半年之后,王振东在近郊一偏僻处租了一间低廉的房屋。总算有了栖身之处,王振东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做画中。
不知是他的画还是他的精神吸引了和他邻居的一位叫王素平的打工女子。她每天都伫立在晨光中默默地望着他背孩子挂着画具包到大街上做画的情景,晚上下班抽空到他屋来看看他做的画,而且还时不时地带上几个哥们姐们来一起观摩。
终于有人关注他的画了,王振东似乎在黑夜的摸索中看到了一丝光亮。他不分昼夜地画着,从那一张张浸透着汗水的国画中,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他的画技像矮子登楼梯一样,在一步步提高。
1996的一天,王素平突然感觉到一种反常,她终于发现:她一向崇拜的那个“画痴”却无缘无故地停笔了,既没见他到大街上做画也没看到他在家里运笔。
她好奇地来到王振东家里:“小王(王振东比她小三岁),这两天咋啦?怎么没看见你画画?”
王振东躺在床上,无力地说:“我手坏了!”
看着他黯然神伤的样子,王素平关切地走过去一看,大吃一惊:他的残臂因骨头与笔杆之间长时间的磨损,皮肉磨破后被感染了,右残臂的截面处已经烂了很深的一个洞。家里更不用说凌乱成什么样了。
看到这个惨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王素平主动地说:“你到医院去看病吧,老躺在家里怎么行?孩子由我带着,你就放心吧!”
王振东不好意思地嗫嚅着:“我没钱看病!”
怎么办?王素平也为难了。要是让她照顾孩子或干什么体力活她决不会皱一下眉,可喧银子钱是硬头货,上哪儿去弄呢?这下还真让她犯难了。
她想起了和她一起打工的那些哥们姐们,找他们大帮小凑或许还能解决问题。
“你就别做好人了,看他现在这样子,以后还得了吗?”那些铁哥们铁姐们一听说要借钱给一个非亲非故的残疾人治病,都一致反对她。
王素平苦口婆心地说:“他现在需要帮助,我们大家帮他一下,只要挺过了这个坎,他就能重新挣到钱。他这么有骨气,一个残疾人比我们有些身体健全的人还要有毅力和自信,我相信他好了以后一定有能力还这笔钱的。”
“你说得倒好,要是万一到时候还不了呢?”无论她怎么说,那些靠出苦力挣小钱的小姐妹们说什么也不愿意把有限的血钱拿出去填“黑洞”。
这下,王素平急了:“算我求你们了,他要是真还不了,我替他还!”
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自己的姐妹能信不过吗!这些哥们姐们纷纷把自己攒下来的钱拿出来借给了她。她揣着借来的三千多块钱,感激的泪水滚滚而下。
看她激动的样子,一个要好的姐妹问她:“素平,你是不是看上他了,诚心想嫁给他?”
“那倒没想过,我只是敬佩他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王素平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她的的确确是被王振东的精神所撼动。
她用自行车推着他到南方大厦附近的一家医院做了第二次手术,他的右臂被截去了一截。她一直守着他在医院里观察了三天三夜。
第四天,他们离开了医院回到家。这时候,王振东的吃喝拉撒全要靠人照顾,而且每周还要用自行车推着他到医院换一次药打一次针。
王素平索性辞去了工作,全身心地照顾起王振东来。
王振东在家养病,王素平也断了经济来源,他们的生活陷入了窘境。五素平开始到外面捡破烂换点钱买点粮食,到菜市场捡些菜叶回来吃。
王振东庆幸自己遇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女人,同时也为自己连累了五素平而感到内心不安。他激动地说:“我一个无手人,你还对我这么好,我……”
“我并没别的意思,只是看你们父子俩无依无靠,生活也没有着落,即使不是我,遇到别人也会这样帮你们的。我只是想帮帮你,因为你让我敬佩!你残疾成这样子还坚持画画,你自强不息的精神让我感动。”接着,她向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这也是她第一次向一个男人坦露着自己的隐私:“以前,我也成过家,丈夫待我不好,整天来赌,什么正事也不做还经常打人。我和他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带着俩孩子和他离了婚,一气之下,我就出来打我来了……”
没想到,她也有着和自己同样不幸的遭遇!王振东从内心怜悯起王素平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和了解,积淀在两人心里的那情愫像压抑已久的火山终于不约而同地爆发了。
自从第一次爱情落荒而逃以后,王振东再也没敢奢望过爱情的降临。没想到爱情却在他身体遭受到第二次重创后悄然而至。
王振东紧紧地搂着王素平:“你跟着我会受拖累的,我的手已经成这样了,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做画,我要是做不了画今后的日子可就更苦了。”
“你不能做画了,我们可以出去捡菜捡破烂,同样能够生活。咱们还可以回老家去,我可以种地,咱们有了粮食就不会挨饿了。我一直在想,四肢健全的人虚度年华不干正经事,要手又有什么用?一个没手的人却干着有手的人也干不出来的事情,没手比有手还强,这种男人才值得我去爱,才值得我去为他付出一切。”
他们的心贴近了!此时此刻,只有两颗心在一起激烈地燃烧着,任何承诺都显得苍白无力,甜言蜜语更是显得多余。
王振东暗暗发誓,一定要画好画来报答她对自己做出的牺牲。
晚上,广州的蚊子特别多,他只好钻进蚊帐里坚持做画,有时一画就是一夜,王素平就陪他一夜。
还是在北京的街上露宿时,王振东顾上了儿子却顾不上自己,从那时起就患上了哮喘,只要画画时间长了或走稍长一点的路就喘不出来气。所以每次王振东做画王素平必须守在一起,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
爱情可以带来力量,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
一个夏日炎炎的傍午,王振东和王素平正在广州街头的树荫下做画时,一个老板模样的中年人径直朝他们走来,问道:“一张画多少钱?”
在大街上,王振东遇到类似的情况多了,他们并不是想买画,只是闲着没事随便问问而已。所以,对此人的问价,王振东并没在意,只是头也不抬地随口说了句:“30块钱一张!”
“那好,你的画我全要了!”老板轻描淡写地说着就从包里掏出了一叠钞票。
王振东和王素平都懵了,两个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临走时,老板说:“你画吧!你每天画多少我就买多少。”
几天以后,老板又差人给他们送来了米面和衣物。
这一年,因为有老板的关照,他做画的心入一下达到了3万多元。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呀!
有家了,爱情花开正艳
王振东对画画已经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他说:“我饭可以不吃,但画不可以不画”,圈内人都戏称他为“画痴”。他的画是把民间艺术和中国的国画结合在一起,有他独特的风格和韵味,倍受画界的重视和好评,在市场上也很受欢迎。
“无手人”的名气越来越大了!
1997年底,王振东带着儿子和王素平回到了河北老家。他们在家乡举行婚礼后,王素平又回到河南把一双儿女接了过来。王振东又有了一个完整而温暖的家。
家的温馨真好!
1998年,王素平用王振东在广州画画的收入在家里办了一个奶牛场,她自己就像一头牛:每天早上3点半就起床,先打扫牛棚,到了4点半就到奶场卖奶,回来后又一口一口地喂刚买的那儿10头小牛。几个小时以后,喂完了又要给一家大小做饭,吃完收拾停当了又到地里忙乎去了。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还要跑两趟北京,把王振东在家里画的画拿到北京潘家园古画市场卖……
妻子超负荷付出,更加激发了王振东的创作欲望。他广交画界朋友,博限取众长。他画的荷花不仅看起来鲜艳欲滴,而且荷叶上的水珠晶莹剔透,水珠流过的痕迹也是栩栩如生。
王振东终于挺过来了,他庆幸遇到了妻子王素平,是她给了他一个完整而又温馨的家,是她的爱情给了他绘画的力量,是她的付出给了他无穷的创作欲望。
王素平是老天给他牵的一桩良缘,是命运赐给他的一段良机!王振东十分珍惜妻子的感情。
和所有的家庭一样,王振东的家庭也曾有过一些磕磕碰碰。他们各自的儿子,那对异姓兄弟经常你打我我骂你闹得不可开交,王素平夹在中间很委屈。再加上妻子整天佝陀螺一样围着这个家转个不停,他担心她迟早会被累垮的。
一天晚上,他跟妻子商量:“现在奶牛也大了,我们雇两个人在家照看一下,我带你出去放松放松。看你整天又累还要受两个儿子的气,我们出去画点画挣点钱,还可以付雇请人的工资。这样,我们既轻松又没多余花钱,多好。”
王振东知道妻子舍不得花钱,也舍不得离开她精心创办的奶牛场,就想出了一个他认为是两全其美的主意。
可妻子却说:“我不怕累,孩子们气就气点,今天气一下明天就高兴了,自家的孩子哪有那么好的?一生气就逃避,那往后还咋活。”
王振东无话可说了。面对如此贤惠、通情达理的妻子,他还能说什么呢?
2003年春节过后,那块一直缠绕着王振东的“心病”越发搅得厉害了,使得他寝食难安。
这些年,他的家境好了,在当地,他也算得上是残疾人中的佼佼者。可他有个愿望,他想办一所残疾人活动中心,让所有的残疾人都能学到一技之长,掌握一种生活的本领。但这需要技术和资金,他想再闯京城,重操街头卖画的旧业,以此积攒资金,引进技术。
又是一个晚上,王振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没想到,这次妻子满口答应下来:“知道你闲不住,家里你是迟早呆不下去的。我跟你去!”
他非常感激妻子的理解,一高兴就故弄风骚地说:“知我者,还是我妻子也!”
王素平嘟了一下嘴说:“就你臭美,我不了解你谁还能了解你?”
2004年春节刚过,王振东就迫不及待地催促妻子赶紧打理行李准备进京。
在西单的地铁通道里,当他们接受笔者采访时,王振东感慨万分地说:“如果没有我的妻子,就没有我的现在。我们这次出来的中心任务就是积累资金、引进人才,回去办残疾人活动中心。我之所以把目光盯在北京,是因为北京人才济济,我想在北京请几个师傅回去,给家里的30多个残疾兄弟们传授一点致富的技术,把他们都带动起来!”
说到这里,站在他身后的王素平说:“他的心思全放在这上面了,他在受到刘京生老师办残疾人活动中心的启示后,一天到晚就想着办他的残疾人活动中心。没办法,我只好跟着他来了。不知道他的想法能不能实现!”
“咋不能实现呢!你没听人说过爱情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吗?我们有了爱情这张保单,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他这番充满自信的话风趣而狂放,在地铁通道里,在众多游人的耳边久久地回荡着……
剪裁霓裳的残疾女
2003年8月24日,在第二届全国残疾人技能大赛中,荣获服装剪裁第一名和国家劳动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的北京女选手丁宝明格外引人注目,只见她靓丽的面容充满着自信,合体的装束衬托出高雅。大赛一结束,记者就蜂拥而至地围着她:“您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她似乎早已深思熟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最想马上把我得冠军的消息告诉我的父亲,他正等着看我的金牌呢!”她一边拄着拐往出走一边回答着,眸子里已经滚动着晶莹的泪珠。谁都不会想到,丁宝明的父亲此时正在医院抢救。她推开围上来的众多记者,不顾一切地坐上车直奔北京市人民医院。
泪水早已模糊了丁宝明的视线,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祈祷着:父亲啊,您千万要挺住呀!女儿这就来看您来啦,您的心血没有白费,女儿夺得冠军 了……
爬行童年,父爱点燃了我生命的灯
1962年10月18日,我出生在北京市百万庄地质科学院的一个普通宿舍里。父亲丁孝石是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经常在外,父母结婚8年以后才有了我。父亲说我是他的“宝贝”,就给我取了个宝贝名字——“宝明”。
一年以后,大弟弟出生了。那时,我还不会走路。我多想走路啊!看着我渴望的目光,母亲就一边抱着弟弟一边教我扶着椅子学走路。
正当我一个人扶着椅子开始走路时,我患难上了小儿麻痹症。从此,我的生活没有了阳光,我再也没走过一步路,走路成了我一生的奢望。
父亲抱着我,像一个无助的孩子,泪流满面。父亲一向是个坚强的人,从不掉一滴眼泪。母亲说,父亲是个孝子,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他强忍住悲痛嘴角都咬出了血也没流一滴泪。
父亲一直以为能出现医疗奇迹,让我重新站立起来。为了治我的病,父亲举债抱着我跑遍了全国的各大医院,只要听说有地方能治我的病,不管是真是假,也不管路途有多么遥远,他都要抱着我求诊。
在我12岁的那年冬天,父亲听长春地质学院一位同学说,长春解放军626医院专治小儿麻痹。父亲一听,少有的笑脸上立刻绽放出花一样的希望。
那时,父亲为我治病已经借了好多债,家里穷得连买一张火车票的钱也拿不出来了,几乎到了釜中生鱼的地步。
父亲见母亲面有难色,心一横:“不管家里穷成什么样,也得去长春给女儿治病!”
父亲第一次放下了他做师长的尊严,连夜去向他的学生们借钱为我治病。当时,在父亲所认识的人中,惟有他的学生他还没伸手向他们借过钱,他知道学生的生活已经相当艰苦了。这一次,为了救我,父亲已别无选择。
看着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整理着借回来的那些零零碎碎的钱,母亲心里好一阵酸楚,她背过身去悄悄地拭着眼泪。
这一切,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朝着母亲身边爬去,轻轻地扯着母亲的裤脚,哭着说:“妈妈,我不想去长春,你让爸爸把钱还给人家吧!”
母亲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转过身一把将我揽在怀里,强打着笑脸哄着我“宝明乖,听爸爸的,去了长春你就能走路了。”
走路?!对于我,这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字眼啊,我终于没再做声了。
不久,父亲的那位同学打来电话说,他们单位要到北京提一辆吉普车,要我们随车一起到长春。父亲好一阵兴奋,因为这样就不用掏钱买车票了。
几天以后,我和父亲随车出发了。
车子在路上颠簸着,越往东北走天气越冷。父亲怕我冻着,就把随身带的被子和毯子全都围在我身上。直到他实在挺不住被冻得瑟瑟发抖时,我才发现父亲只穿着一套攀登服。
晚上,车子停在了路边的一家旅馆。父亲不敢动用那借来给我治病的一分一厘都被他看得像生命一样贵重的救合钱去住旅馆,在旅馆传达室,父亲和值班的工作人员商量,借用值班员的床铺让我躺一晚上。
好心的值班员十分同情我们,让我在他床上躺了一夜,而父亲一直坐在床边守着我。
我们就这样捱过了4天时间。到了长春,父亲的脚已经冻得又红又肿,下了车,他不顾一切地抱着我背起行李一瘸一拐地直奔626医院。
在长春626医院。父亲一直陪着我呆了7个月。这是怎样的7个月呀!我做了切骨手术以后,父亲每天帮助我锻炼,压腿、负重……我受的罪不小,吃的苦更大。病房里没有父亲的歇息之处,他只有整夜整夜地坐在椅子上打盹。
也许,这就是命。7个月后,我却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我的病现代医学界已无能为力!
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下子瘫坐在我病床前,拼命地扯着自己的头发,声嘶力竭地对天长啸:“苍天啦,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的女儿呀!”
那一刻,父亲好像突然间苍老了十岁。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似乎突然间长大了,我不再哭着嚷着要走路,我鼓励着自己去坚强地面对现实。
我安慰父亲:“爸爸,您不要伤心,这次虽然没治好我生理上的病,却医好了我心理上的病,这比什么都重要。”此时此刻,是他那博大的父爱点燃了我生命的长灯。
我至今仍难以忘怀:
当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时,和我同龄的小伙伴们一个个都蹦蹦跳跳地上学了,我却只能爬在地上眼馋地望着他们发呆。父亲却早已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在同龄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去上学的时候,父亲已经在为我联系学校了。
由于我生活不能自理,父亲联系了几所学校,人家都拒绝了。可是父亲已经下定决心,不管怎么说一定得让我读书。他只好再次到附近的百万庄小学去求校长,给学校承诺:保证半天内不上厕所,不给老师添麻烦。父亲的诚心感动了校长,终于有学校接纳我了。
那天,一大早,母亲就起来给我梳洗,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父亲背着我,母亲跟在后面背着我的书包,把我送进了学校。
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的生命里开始有了信念、理想、追求和快乐,有了和其他小伙伴们一样的幸福童年。
人生如戏,我要扮演王侯决不扮演乞丐
自幼在小孩们的歧视和骂声长大的我,养成了争强好胜的性格,凡事都不甘落后。尽管我一边治病一边上学,因治病耽误了不少学习时间,可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
初三那年,听说学习成绩好的可以考中专、技校、军校,这样就能提前参加工作,我激动得彻夜未卢眠。按当时的成绩,我考中专没有一点问题,我也想提前参加工作,为家里挣钱还债。
父亲为我参谋,建议我报考财会专业。
中考成绩下来了,我的考试成绩相当高。如我所愿,我被一所中专的财会专业预录了。我激动的心快要跳出来了,我开始设计着未来,设计着怎样去报答父母、服务社会、实现自身的价值。
体检那天,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兴高采烈地向医院驶去。医院里,等着体检的人很多,我拄着拐站在体检的人流中。仿佛是我的介入给这个神圣的场所增加了一份不和谐的音符,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朝我射了过来。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嘻嘻,你看她那样子,哪个学校要这种人呀。”
这声音不大,但很刺耳。父亲大概听到了,我已经感觉到父亲的那两声“咳嗽”明显地带着一种不可侵犯的威严和警告。
我早已习惯了这种不是善意但也说不上是恶意的“提醒”,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只是想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和价值——一种和健全人同等的竞争条件。
可令我沮丧的是,正式录取时终于因为我身体和残疾而被无情地刷了下来。我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心!
虽然有点寒心,但我仍然不服气。我想,中专上不了我就上高中,将来考大学。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伴随着我,在高中的学习阶段,我的成绩一直出类拔萃。
1980年7月,我盼望已久的高考临近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正当我满怀信心地准备参加高考时,却传来了“残疾人不能参加高考”的消息。这一次,我真正感到了失望,我的精神,我的信念就在那一刻遭到了最残酷的摧毁。我像一具失去了灵魂的躯壳,訇然瘫倒下去,再没有力量爬起来。
就在我倒下去的时候,父亲挺身而出。万事不求人的父亲破例亲自带着我长到市教育局招生办:“我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请求你们,请你们网开一面,让我的残疾女儿参加高考吧!她只是腿残了,可她的思维却相当敏捷。我可以保证,她的智商和人品都是出类拔萃的。如果她考上了大学,她会更加努力的。”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残疾人拒之门外呢?”我也开始愤愤不平了。
负责招生的工作人员看了看我,然后仍然坚持着他们的原则:“你知道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得花多少钱吗?所以不能培养你这样的残疾人。”硬绑绑的话气得我半天喘不过气来。
回到家,父亲和母亲就到处张罗给我找工作。可是找来找去却没有一个单位肯接受我这样的残疾人。上学没人要,上班又没单位接受。受到三次打击的我终于不堪重负了,我的情绪感坏到了极点。那些天,我过着没有钟点的日子,常常呆在家里不吃不喝一睡就是一天。
母亲怕我想不开会闹出什么事来,就安慰我说:“你别着急,我们想办法给你找个工作,万一找不到,爸妈也养得起你,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呀。”
我常常一个人呆在家里对天长叹:上帝啊,你怎么这样不公平啊,从小你不让我走路,这么多年来我刻苦学习不就是为了今后自己挣碗饭吃吗,可到头来你连饭碗都不肯给我一个。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在我抱怨世事不公时,父亲拿着一本书对我说:“宝明,爸爸送你一本书,你在家没事就好好看看吧。”这是一个日本作家写的书,是关于人生和命运的。
自从高中毕业后我就不再看书了,因为我知道书对我已经失去了意义,可是父亲推荐的书却不能不看。
我恭恭敬敬地打开书,扉页上被划了重重红线的两行字使我已经成为死水的心田里激起了阵阵微澜。上面写着:人生好比一台戏,优秀的演员可能扮演乞丐,而拙劣的演员却可能扮演王侯。这是多么富有哲理的人生箴言啊!我恍然大悟,立刻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我知道,这是父亲在启发我,要我自己选择在人生的舞台上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父亲历来都是这样,对于我的教育就像他带学生那样:施于启发,从不强加于人。这就是父亲,一个在我每一次人生关键时刻都给了我最有效帮助的导师。
我暗暗地发誓:爸爸,您放心吧,女儿明白了。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一定要扮演王侯决不扮演乞丐!
打那以后,我就开始学服装制作。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缝制服装,还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帮同学缝衣服,家里谁的衣服短了我就自己接,衣服破了自己补。
没有师傅教,我就买书照着学。学着学着,我突然感觉自己在这方面有天赋、有悟性,也特有灵感。
1984年,我拿到了个体营业执照顾,开始在家里正式开张营业了。虽然当时名气不大,活儿也不多,顶多就揽一些改改补补的小生意。但不管是大活还是小活,我都一视同仁认真对待。
我越干心里越亮堂,越干心情越快乐。渐渐地,由于我的优质服务和快乐的性格吸引了众多的顾客,我的生意开始红火起来。
我虽然残疾了,但我仍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态度。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愿意跟快乐的人在一起。
我干服装这一行,每天要面对很多顾客,我总是把内心的喜悦和快乐送给对方,把不快和烦恼留给自己。我自己都有一种感觉,老和一个爱抱急的人、一个爱发牢骚的人、一个心态不好的人在一起就觉得窝火、压抑、难受。所以,这么多年,我的顾客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说:“宝明,大家和你在一起,根本没觉得你是一个残疾人,你要不说出残疾这个词来我们还真忘了。我们这么多健全的人都还想跟着你走。”
这是我的顾客对我的最好褒奖,我感到十分满足,我已经从一具“乞丐”演变成了“王侯”。
天遂人愿,我在父亲弥留之时捧回了金牌
1994年,我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服装设计系。1996年毕业以后,我注册了用我的名字命名的“宝明服装制衣”专为高级白领、知名人士、演艺明星包装设计服装。2002年,我又注册了“小博士服装有限公司”,专门制作学生校服和教师职业装。
我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个服装生产厂,我本着“不做最大,要做最佳”的经营理念,吸引了众多的顾客。
1997年的一天,我店里突然来了一位贵客:邓朴方的姐姐邓琳。她一边选料一边说:“我是特体,衣服不好做。”我看了她的体型,很快就为她设计好了款式。就在我拄拐起身为她量体时,她惊讶地说:“我的朋友只说你服装做得好,可没说你是残疾人呀。”我笑了笑,说:“怎么样?没吓着你吧!”她一听,也跟着笑了起来。当她穿上我为她度身定做的服装时,满意地说:“小丁真行,有前途!”
2000年,残疾人指挥家舟舟,第一次指挥国家级乐队演出。一大早,中残联的一位领导给我打来电话:“宝明,现在交给你一项紧急任务,请你马上给舟舟赶制一款正式的指挥服,时间很紧,后天要货。舟舟一在一个小时后下飞机,你赶到机场为他量体。”末了,这位领导又补充道:“服装要做得与指挥家的一模一样,因为这场演出是一个智残的孩子指挥国家一级乐团,这在中外都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他的形象很重要。
我两天两夜没合眼,直到我满意了,才把衣服做好送过去。当我看到舟舟穿着我为他设计的指挥服在国家大剧院非常成功的演出时,我的内心再次涌动出一种成就感。
这些年,我专门为残疾演员孙晓梅、李琛、金元辉、孙岩等设计制作过演出服装,也为陈慕华、吴仪、何鱼丽、彭佩云、林文漪等20多位领导人设计制作过服装。多年来,我亲手缝制的了国人员服装到了世界20多个国家,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我终于成功了,就在我蹬在父亲的肩膀上摘取桂冠时,父亲却病倒了。
2003年7月底,父亲因肺病复发住进了医院。
8月2日,我接到了市残联的通知,要我从8月4日开始参加为时半个月的全国第二届残疾人技能大赛决赛前的集训。
想着危重的父亲,我犹豫了:一边是为了我而呕心沥血的父亲,一边是我毕生追求的事业,两边都需要我,我该怎么办呢?
还是母亲了解女儿的心思,妈妈拉着我的手说:“宝明,你就去吧,家里这边有我呐。要真有什么事我就给你打电话,你就放心去吧!”
8月3日临走之前,我在医院里陪了父亲一天。父亲气若游丝地问我:“什么时候决赛呀?我要等着看你的金牌!”父亲在住院前已经知道我要参加决赛。心里还一直挂念着。
我的心一阵紧缩,我连忙凑近父亲的耳边说:“爸爸,我明天就要去参加培训了,过几天就回来,你一定要挺住,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女儿一定要给你拿金牌回来!”
父亲很累,已经说不动话了。
我握住父亲那双皮包骨头的手说:“爸,您要是听明白了,就眨一下眼睛。”
父亲努力地眨了一下眼。从父亲的眼神中,我已经读懂了父亲对我的企盼和鼓励。
就这样,8月4日,我含着热泪依依告别了父亲去参加集训了。
北京的8月,酷热难当。我们六各参赛跑选手集中在一个没有空调的教室里,四只大功率的电熨斗散发出来的热量使室内温度一下子升高了许多。我们夜以继日地挥汗苦练着。
集训的第二天,北京市副市长孙安民和市残孙的赵春鸾理事长到集训基地来看我们。残联的一位同志向孙市长介绍说:“丁宝明这次能来真不容易呀,参加集训前她父亲正在医院抢救。”
孙市长一听,对秘书指示道:“马上和医院联系,要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派最好的医生护士,用最好的药,保证丁宝明的父亲不能出现意外,一定要让老人家能听到女儿的好消息。”
赵理事长也安慰我说:“宝明呀,你就安心地好好地参加培训吧,家里和医院那边我们都会安排好的。”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摧人奋进的呢?我放上一切包袱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培训之中。
集训的日子相当艰苦,有好多次我差一点坚持不下去了,可一想到躺在病床上等着我消息的父亲,我一咬牙,挺了过去。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心灵感应”吧,父亲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支撑着我、鼓舞着我。
8月22日上午8点,我和来自全国的50多名同一项目的优秀参赛跑选手走进了考场。因为有个信念在支撑着我,所以我临场发挥得相当不错。4个小时后,我一身轻松地走出了考场。
8月24日,闭幕式。
在宣布成绩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紧张得“突突”直跳。终于开始宣布服装类的项目了,当主持人宣布:服装剪裁第一名——丁宝明!我怀不自禁地“啊”了一声,眼泪夺眶而出。要知道,各项目的第一名选手还要参加11月份的国际大赛跑呀!
这下,总算给父亲有个交待了。颁奖一结束,我拨开纷纷围上来的记者,马不停蹄地直奔市只民医院。
当我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深度昏迷好几天了。我一下子扑在父亲病床前,声泪俱下地叫着:“爸爸,我回来了,女儿真的拿到金牌了。您快睁开眼睛看看吧!”
我把金牌贴在父亲的脸上,哽咽着:“爸,这就是女儿捧回来的金牌,您瞧瞧呀!”
好一会儿,我发现父亲的嘴唇嚅动工了一下,一颗泪珠从父亲的眼角滚落下来。我知道,那是父亲激动的泪水、自豪的泪水,是父亲喜极而泣啊!
8月26日一早,父亲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我们。他走的是那样的坦然,那样安详!
父亲哟,您在天国还会关注女儿参加世界比赛的消息吗?
(丁宝明口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