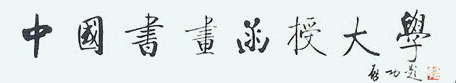老砖井
民国三十六年春天,一顶小轿把莲二奶奶抬到河西银沙屯张家。
莲二奶奶当时正值二九妙龄。花一样的娇艳,水一般的柔情。红绸子盖头一揭下来,映得小土屋里四壁生辉,满堂溢彩。老少姐们见了都说她赛过杨柳青画儿上走下来的美人儿。丈夫张石柱,二十出头的年纪,生得魁伟英俊。一副磨扇般的胸膛,像是憋着永远也使不完的力气。
村头有祖上传下来的二亩菜地,河边有三亩旱涝保收的蒙金夜潮地。日出而耕,小两口一个像下凡的织女,一个又似那勤劳的牛郎;挑水浇园,赶集卖菜,春种夏管,秋收冬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日落而息,两间土房又成了水中小岛,栖息着一对恩爱的鸳鸯。豆油灯一灭,俩人便拥在一起,倾吐那些永远也吐不完的体己话。
“哎!莲子,人家说新婚男女如干柴遇烈火,沾上就有。都一年了,你咋还杨柳细腰呀?”
“去!”莲二奶奶轻轻地打了丈夫一巴掌,“瞧你急的,生孩子有啥难的。等俺生了个开头,会像母鸡下蛋似的,一撅屁股就生一个,怕你养不起呢。”她说完这俏皮话,臊得一个劲儿往男人怀里扎。
“莲子,俺合计好了。完秋卖了地里的收成,再搭上这一年的菜钱,咱就在自家的园子里做上一口井。省得到王财主家里挑水,老是瞧人家的脸子屁股。自己的井,咱用着硬气。”
“嗯,俺听你的。”莲二奶奶一双纤手,抚摸着丈夫被扁担压肿的肩膀。“等咱有了孩子,再也不用像你这样受累了。”
人有旦夕祸福。
高粱红脸儿,谷子弯腰的时候,石柱在河边地里归置庄嫁,被国民党军队抓去修工事。这时莲子已有身孕,硬是撑着重身子,把里里外外收拾的井井有条。她盼着,丈夫能早一天回家。
事与愿违。如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军队驻守半个月,又向南败退。张石柱被溃军裹着当脚夫,一去不返。莲二奶奶有些绝望了。
她结绳记数,一天一个扣儿。当结满四十几个扣时,一个从半道上跑回来的同乡带来音讯:张石柱没有死,他被补了缺,大概去了海的那边……
莲二奶奶眼里,又燃起希望之火。她把全年的收成,换了半口袋“金圆券”。谁知物价一天一个样儿,那些纸票子变得比手纸还贱,除她谁还敢要。她又找到跑地掮的魏老三,典出了河边的三亩夜潮地,换来了砖木石片。她要完成丈夫的夙愿,做一口砖井。等丈夫一回来,她就捧上一碗清澈的井水,送到他面前……
树叶飘落的时候,砖井动工了。那气派,全村都少见!百里闻名的风水先生小神仙给看的水脉。临走时夸下海口:说照他选择的井位开掘,此井必有两个泉眼,与北寺后面“二龙坑”相连,永不干竭。莲二奶奶听了,惊喜交加,当时便打发人给小神仙送去了两担玉米。
做井这活儿,女人是不能上前的。特别是双身子女人,更不能越雷池半步。莲二奶奶让村上刘三爷给承头,请来工匠。抢茬那天,足有几十号人,光猪肉炖粉条就吃了一九刃锅。
砖井做好没多久,莲二奶奶生下个男孩,取名为盼娃子。
盼娃子满街撒野的时候,莲二奶奶的砖井和菜园子一起都入了社。
时过境迁。
庄户人的日子红火了,莲二奶奶也已年过花甲。岁月的坎坷磨难,使她落个病秧秧的身子,活像棵焦梢的老树。年轻时美貌柔情和那一股子心劲儿,早被岁月的河流冲失,寻不到一点影子了。她忧郁寡欢,神情恍惚,除去压在心底的一丝企盼外,世间的一切都在她的心里淡化了。自从吃上自来水,那口老砖井就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变得无人光顾了。只有莲二奶奶每天出现在井边上,默默地转悠一会儿。天长日久,竟在井口周围,踏出一条圆圆的小道。
盼娃子自幼聪明伶俐,长大后更是出人头地。政策刚一开放,他就承包了一个厂子,几年下来已是腰缠万贯了。他扒了那两间小土屋,建起一幢漂亮的小楼。为给村里壮门面,小楼就盖在村头老砖井旁边。搬进小楼以后,盼娃子出来进去,总瞧着那口老砖井别扭,便要把它填死。这下可惹恼了莲二奶奶,她把儿子指鼻子挖眼骂了三天。盼娃子生来孝顺寡母,不敢当面违抗,背地里把媳妇使唤出来。
媳妇凭着一副伶牙俐齿,以怕孩子玩耍时掉进去为由,举出一堆道理,终于说服了莲二奶奶。老砖井被一副沉重的碾盘压在下面。从此,莲二奶奶闭门不出,独自在那间四周壁纸,顶上吊灯的房间里消耗时光。
两年后,莲二奶奶不行了,十来天水米没打牙,躺在排子上,就是咽不下那口气。盼娃子伏下身,轻声问老母还惦念什么。莲二奶奶双目紧闭,说想喝口老砖井的水。众人疑惑,只见她嘴里嚅动着,发出微弱的声音:“小神仙说的,那井……永不干竭……”
老母临终一愿,盼娃子怎敢怠慢。他找来几个小伙子,撬开碾盘,顿时一股潮气冲天。再细看,只见井底崩塌,乱砖淤泥。盼娃子急得直跺脚,倒是一位本家嫂子出个主意,让盼娃子接了碗自来水,端到老母嘴边。只见莲二奶奶睁开双目 ,浑浊中透出一丝光亮。断断续续地说道:“你爹要是回来……让他尝尝老砖井的水。告诉他……我一直等……”话没说完,便合上眼皮。
众人恍然大悟,惊诧之后,一片嚎啕声。
刘三爷
在村上,刘三爷可算个人物儿。
我还穿着开裆裤的时候,刘三爷就六十开外了。村上谁家有红白喜事儿,都得请刘三爷。到了事主儿家,事主儿也不和他客套,只交待一句:
“三爷,这事儿可全瞧您说了。”
这话其实也多余。刘三爷知道是干什么来的。他找到支客,用一种不容妥协的口吻说道:
“派俩人,跟我走。”
干啥?红事儿借盘子借碗借桌椅板凳;白事儿借杠借锹借绳套麻纰子。村上谁家有这些东西,全装在刘三爷肚里。到了哪家,刘三爷推门就进,挺着肚皮往院里一站。看家的不管是嫂子大妈还是侄、弟媳妇,见刘三爷来了,也不多问赶紧给归置东西。刘三爷让俩跟班儿把东西清点记数,装车入篮。完了,再打几句哈哈,这才去下一家儿。也有的吝啬婆娘,怕用坏了自家的东西,跟他瞒瞒哄哄,不愿借。刘三爷不恼也不火。返身就往外走,临出门只说一句:
“行!有肉不吃耍骨头,不让你亲自送去你脚板儿痒痒。”
等那家爷儿们回来了,听说刘三爷是空手回去的,立刻责骂婆娘:
“真他妈瞎了眼!竟让刘三爷白跑了一趟。赶咱有事儿,三爷给你撂了。”
婆娘麻利儿地把东西送到事儿主家里,还得跟刘三爷赔理道歉。刘三爷大人大度,哈哈一笑 :
“行了,都是明理儿人。赶你娶儿媳妇、聘闺女,做百八十桌,三爷我全包。”
忙活完了,刘三爷从不用事主儿的谢酬,只是临走时,大大方方地往怀里揣瓶酒。遇上理儿多的事主儿,多送他几步,他就一挥手。
“都回屋歇着。玩儿虚的,下次甭找我!”事主儿马上止步。咋的?怕刘三爷恼了。他就这副脾气,天性豪爽、豁达,还有点顺毛驴子。你捧他、顺他,他就跟你掏心窝子。村上大姑娘、小媳妇、大小孩芽儿,叫他声三爷,可以由性儿和他逗闷子、砸法子。你要呛他,那你算碰上硬的了。
经我眼见,村东头王老二家办事儿,臭牙帮子三圣给落忙。一桌喝酒的时候,刘三爷放了个屁,三圣见景生情,胡吣了一个故事:说三国时曹操和手下将领一起吃饭,曹操放了一个屁,手下怕曹操尴尬,都说是自己放的。没想曹操正赶气不顺,一摆手喝到:“非也,乃是我操之屁也。”
三圣嘴尖舌巧,骂人不带脏字。刘三爷可不是三五儿赶集,四六儿不懂的主儿。啥话听不出来,酒杯一下甩到三圣脸上,骂得三圣直眨巴眼睛:
“你小子来这套,毛嫩儿!告儿你,我酒桌儿上掏嘎拔份儿的时候,你还卢沟桥老豆腐––––红白两盛着呢。”
打那儿,三圣见了刘三爷就躲。
刘三爷的话,也不算夸张。早年,他在通州城里开过绸缎庄,整天泡在肉山酒海麻将桌上。买卖赔了,还让债主扒光衣服,光屁股回到村上。
刘三爷后辈子只干两样,冬天打更,夏天看青。这活儿没啥技巧,可刘三爷干得让人心服口服。冬天,不管多黑,多冷,刘三爷闷上几两酒,把酒瓶子往怀里一揣,拿根铁通条,可街筒子一转。乡亲们敞门睡觉,心里踏实。夏天,满园子青菜,一地庄稼,刘三爷披个大夹袄,这躲躲,那猫猫,冷不丁地大手电一扫,想偷摸的人连边也不敢靠。
刘三爷七十三岁那年,得暴病死了。
这些年,村上红白喜事还照样办。可五、六个人出去借家伙,还时常抓瞎儿。上了年纪的人看了,不无感慨地说:
“要是刘三爷活着,这点事儿,他一个人满办。
1992年6月
老场
这是一个废弃的老场,长满了荒蒿野草,只有看场人住过的土坯小屋,孤伶伶地立在老场中央,在蓝砖红瓦的村落衬托下,透着几分久远和凄凉。
初冬的一个傍晚,村上来了一拨打铁匠。在街里转悠一阵儿后,发现了老场这块宝地。小场屋里安下营寨,便支起炉灶,“叮叮当当”地忙活起来。
村上的男人最爱贪热闹,遇上这样开眼事,自然少不了凑份子。闷葫芦来旺遛到老场的时候,大卵子宝圣早在人群里白活上了:
“哎!我说老少爷们儿,咱三两白干儿半斤猪肉下了肚,还他妈伸腰懒得动弹呢!瞧人家,窝头就白菜汤,干的却有心有肠的。啧,咋想的!”
“我说大卵子,你少在这幸灾乐祸。干这行的都是从苦地方来的。想吃香喝辣,有嘛?”来旺平时最看不惯拿穷人打糠灯,呵斥道。
“嗐!来旺,你算哪棵葱呀?你可怜他们,把你家挡腰的东西拿来让人家享用呀!”宝圣翻着一对死羊眼,晃着猪尿脬脑袋,洋洋得意地将了来旺一军。
“拿就拿!”来旺一跺脚,向大伙招呼到,“老少爷们,怜贫嫉富,乐善好施是咱村风祖德。大伙都回去拆兑拆兑,咱养了孩子让他朝上长。”
不大工夫,来旺端来排骨馒头,众人也相继从家里拿来吃食。打铁匠们暂停了手里的活计,风扫残云般地吞咽起来。
“来旺,来旺哥!”
不远处,臭屁股嘴马根喊叫着冲进人群,一把抻出来喊:“我到处找你,敢情在这儿夸富比阔呢!”
“嗐,富人求一斗,穷人求一口。苦地方来的,咱不该接济接济吗。”
“哎哟老哥哎!你可真是眼睛窝子浅,屁股沟子深。他们这号人穷?告诉你:家家是小洋楼,使的,一水儿电器化。比咱强多了。”
“啥?你说的当真!”来旺瞪大眼睛,盯着马根。
“绝对当真,骗你我是爬着的。”马根撇着大嘴,一副卖弄的样子,“这几年咱兄弟走南闯北捣腾买卖,这号蒙人捣鬼的事见过多了。不装出一副可怜样儿,你能给吃给喝给票子?”
“妈的!”来旺听完,一股嫉火油然而起。他冲进人群,劈手抢过铁匠们手中馒头,扔给了身边的一条大黄狗。心里道:富得流油,却在这哄吃喝,有东西还喂狗呢。
大黄狗呜呼一声,头动尾巴摇地扑向地上的馒头。宝圣也乘机抢过铁匠眼前的排骨,边吃边嘟囔:“来旺哥,其实我这两天正断顿。那我就替他享用啦!”
“你小子就会捡漏。不够吃再上我家里端去。”
来旺说完,悻悻地走出人群。
磕巴三叔
听奶奶说,生我的那个春天,“瓜菜代”刚过,家里秃天刮地。老娘婆子跑惯了腿,吃惯了嘴。怪罪面条汤里没给放鸡蛋,还没等把我接下来,便下炕溜了。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是磕巴三叔卸下了驾车的黄辕马,一路飞奔,给在县上工作的父亲报了信,弄了辆汽车把母亲送城里医院,我才得以安然降生。隔了几天,又是磕巴三叔甩着红缨子大鞭把我们母子接回家中。
和磕巴三叔在一起,奶奶放心。她常念叨:“你磕巴三叔是好人。家虽穷,有骨气。谁家有个为难着窄的,求他,准血了心帮忙。只可惜,他从小就爱摆弄牲口,除子赶车,不会别的。他离不开牲口呀!”
长大几岁,我学野了。成天和一帮小子们在大街戏闹,看磕巴三叔赶车。重车时,磕巴三叔从不坐在车上,而是手握鞭子和辕马同行。说这叫马借人力。只有空车,磕巴三叔才坐在车上,晃着鞭子,悠闲的神情,像是给个县官都不换。车到眼前,我们几个一起往上爬。磕巴三叔说不出整齐话,急得往我们头上抽鞭子。我们赶紧溜下来,一边跑一边喊:“磕巴磕,赶大车。不让上,就翻车。”后来,我听人家说,三叔最忌讳别人叫他磕巴。由于家穷和这个缺陷,他近四十岁还没有讨到女人。
自从上了小学,我和三叔见面就有时有晌了。我住的庄子靠着京榆公路,一到冬闲,这一带的大车都出来拉脚,往北京建筑工地拉石料。所以马蹄声声,彻夜不断。我问奶奶:“这里有三叔的车吗?”
“你三叔不赶车了。”奶奶摇摇头。
“为什么?”我急了,像上次考试没有及格。
“冬天拉脚能挣补助,让队长儿子给顶了。你三叔干什么都有骨气,唯独放不下牲口,惦念着牲口,不让他赶车,等于要了他的命呀!”奶奶叹着气。
不久,我转到城里上学。后来,又参加了工作,安了家。庄上的事便知道的很少。只记得家里来信说,磕巴三叔在五十岁的时候,被一个外地媳妇招去做了上门女婿。那个女人有些点脚儿。磕巴三叔开始不愿意,后来还是去了。因为她家有一挂新栓的大车。
1991年5月20日
祖父
我早就想写一篇关于祖父的文章,可当他带着一脸的安详,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的文章却没有写出来。
为此我常常感到内疚和悔恨。
在我少年的印象中,祖父应该永远不会老的。二十多年前,已年近古稀的他,说出话来声似洪钟,走起路来两脚生风。村里将上百亩园田春种夏管,秋收冬藏的重任托付给他。每天早晨,我都能看见祖父站在渠埂或一个高坎处,几个手势,几声吆喝,男女劳力便按照他的旨意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那情形,好像一个身经百战,指挥若定的资深老帅。
生产队解体后,家里承包了几亩地和一点儿菜田。祖父的身影,又时时隐现在自家的绿海田园里。长年的劳作,使他练就了一副强劲的筋骨。祖父八十多岁的时候,还主动到田里挖渠引水,开沟播种。每逢节假日,居住在外的儿孙们携大带小回到家里,在一片“爸爸”“爷爷”“太爷爷”的呼应声中,祖父品着杯里的白酒,瞧着同堂四世吞咽着他的劳动果实,饱经风霜的脸就会喜得像一朵绽开的墨菊。一种舍此别无它求的满足感从内心向外流淌着。祖父襟怀坦白,开朗豪放,淡泊名利的性格是村上人无不知晓的。听同族一个长辈讲,解放前,祖父在北京大栅栏开过一个颇有名气的“凯星”鞋店。后由于不慎失火,毗连了周围的店铺而被起诉入狱。当时的法官为达到敲榨目的,暗里授意祖父是周边一个店主所为。祖父光明磊落,宁是承受了十几次热堂之苦,也没有按照那个法官的意愿去做。祖父被保释出狱后,已厌倦了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和官场上的黑暗腐败,毅然扑向家乡这块土地。
祖父前半生经商,后大半世务农,天生不懂积攒钱财,所以也没给家里留下什么。母亲对此颇有微词,说是白顶了一副“瓦房刘家”的桂冠(我们家族有一所祖上传下来的很有名气的老屋)。祖父从城里回来不久,新中国成立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以至以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祖父作为一个见过世面,通晓文墨的人自然有许多被吸纳各种组织的机遇。在当时一些人利用各式运动发泄私愤,指鹿为马,损人利己已经司空见惯的情况下,祖父却心静如水,独善其身。以摆正一颗心,管好手中笔。是非有公论,成人舍己的信条约束自己。使村上许多无辜之人免遭冤家错案的株连。
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祖父终于老了。实实在在的老了。
去年秋末,我回家看望祖父。从他那拄着拐杖,迈出颤微微的步伐中,我好像看到一个裸暴在春阳下的雪人,随时都有融化的可能。惊诧之余,我酸楚地感到:祖父离寿终正寝的日子恐怕不远了。
事隔半月之久,我果然接到家中的电话,说祖父不行了。我匆忙赶到时,祖父已是神情恍惚。我等待许久,终于在他回光返照之际,和他说了几句我想要说的话。
祖父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根本没有显出世人所描绘的临死前的那种痛苦,只是频频地皱了几下眉。
村上人都说,祖父没什么病,纯属老死的。这种幸福的死亡,只有在一生积德行善人的身上才能体现。我不是唯心主义者,但乡亲们这种说法,我信。
1999年4月
大脚二姥
从娘家那边论,大脚二姥是姥姥的一个远房堂妹。
大脚二姥快人快语,五大三粗。据说天生一副放荡不羁的性格。十多岁该裹脚的年龄,她娘帮她前脚儿裹,她后脚儿放,一离眼儿,早颠儿外边野跑去了,她娘唉声叹气:“你一双大脚,将来哪个好主儿娶你!”
“嫁个浪荡帮子窝囊废,我情愿!”二姥甩出这么一句。
这话像一锤定音。当二姥快到烂在家里的年龄,由姥姥牵线搭桥,果真嫁给了我那一脚踢不出仨响屁的二姥爷。
哥几个混到马勺净碰锅沿儿的时候,便想起分家。二姥凭借一身邪力,一双大脚,一副伶牙俐齿,分地,调垄划线埋界桩;分房,瞧柁数檩量尺寸,像个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事事冲在前边。分浮财那天,兄弟五人为仅有的一头肥猪争持不下。中人赶忙斡旋:屠宰按块分割。三姥爷出个嘎咕主意:每人编一句打油诗,表明自己所要的部位。姥爷行大,便有涵养地向下推辞。二姥爷憋的面红耳赤,支吾半天楞没挤出一个字。三姥爷当仁不让,一瞄桌上茶盅,出口成章:“茶喝十遍色变纯,我要前臀和后臀。”四姥爷也不示弱:“庄稼无肥长不旺,我要肥猪的五脏。”五姥爷一看再不言语,就没份儿了,紧跟一句:“夏穿单衣冬盖被,我要头蹄和两肋。”
转眼工夫,一头肥猪被瓜分得爪干毛净。二姥在窗外可绷不住劲儿了,她一步跨进屋里,盯着三姥爷:“主意是你出的,说话算数不?”
“不算数我不成蹲着撒尿的啦。”
“好听!”二姥上去就解二姥爷裤带,一屋人蒙了,中人赶忙劝阻,二姥说:“爷们儿有刀我有鞘,一头肥猪我全要。”
红口白牙,收回晚矣,惯于抓尖抢上的三姥爷蔫了。尚未屠宰的肥猪,自然轰到二姥的圈里。
二姥把肥猪又精心喂养起来,造了好多粪 ,全施到刚分的青苗地里,把那六亩春棒子催得咔吧咔吧地朝上长。粪积足后,二姥把猪卖了,二一添作五,将钱悄悄塞给四个妯娌。
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正临粮食还家的时候,日本鬼子打过来了,在白庙渡口两边修起高高的炮楼。
二姥打发二姥爷去河东枣林庄买筐,回来时,被鬼子哨兵截住。二姥爷胆小,撒脚就跑,鬼子朝他开了枪,尸首扔在地窨子里。二姥听说后,一口气憋成了“气迷心”。从此二姥用链绳栓着一个破筐,每天在大街小巷拉着,边走边嘟囔:“当家的,筐有啦,你快回来吧……”
我记事的时候,二姥剩下那身高大的骨架和一双发直的眼睛,被她唯一的儿子奉养着。
1999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