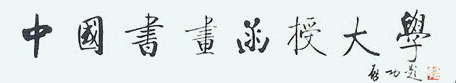南蛮子•白丫
小镇实在小得可怜。两条马路交叉而过,十字道口便构成了最繁华的街景。
十字道口的沿路两侧,散落着几家店铺,常年经营着油盐酱醋等几样相同商品。只是到了春天,有的铺子门口才摆上几捆菠菜小葱水萝卜什么的,且都是自己家园里出产的。店主们管这叫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儿。
忽然有一天,小镇上来了个白脸南蛮子。说是要在十字路口开一家时装屋,小镇马上掀起了一阵微澜。南蛮子租了王三寡妇的两间临街房。镇上的人家一般都忌讳向外来人出租房屋,但王三寡妇无依无靠, 稀罕那仨瓜俩枣的租费,就应允了。
南蛮子做生意和镇上人不同。他把两间屋子做睡房、仓库。却在屋外的两树之间,从低至高拴上三道铁丝,上面挂满花花绿绿的货品,引得镇上的女人经过时,一眼一眼地往上瞟。令南蛮子没有料到的是,幌子挂出去十几天,只有一个被唤作白丫的姑娘光临过几次。
白丫不姓白,长得也不白。不过她从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打扮。凑个块儿八毛的就到小店里买瓶低档化妆品,往脸上厚厚地涂抹一层。惹得镇上的半大小子们说她先刮腻子后喷浆,凉驴粪蛋挂层霜。不温不火的绰号因此而得。
白丫光临时,手里总是攥着把瓜籽,倚在挂着货品的树干上。嘴唇灵巧地上下翻动着,边吃边和南蛮子扯闲篇。南蛮子正需有人给他答疑解惑,便问白丫镇上的人为何不买他的东西。白丫把嘴往上一努,说瞧你挂的那些玩艺儿,谁好过来。南蛮子乍一听,以为嫌他货品不好。可顺着白丫努嘴的方向一看,那高处挂的全是女人用的胸罩、内裤一类。南蛮子恍然大悟,说既是这样我就收起来吧,不然别的货品也没法卖。白丫笑他:“藏起来谁还知道你有这些玩艺儿。别看她们不过来,心里早稀罕上了。你找人暗地一串合,不就结了。”南蛮子一拍脑门儿,对呀!我看你就行。赚了,我不会亏你。白丫一乐,说那我试试吧。从此,南蛮子每天早晨依旧用一根小竹杆将那些扎眼的女人用品挂在高处,然后就坐在竹椅上看书。随着白丫进进出出,他屋里装满货品的大袋子,鼓了又瘪,瘪了又鼓。
几个月后,南蛮子忽然觉得有些异常。白丫好几天没来取货了。挂在高处的那些货品,招来的尽是男人们敌意的目光。白丫给南蛮子暗地里做掮客,是瞒着家里的。可经她手卖给镇上年轻媳妇的东西,是难以瞒住她们的男人的。男人起初发现自己的女人褪掉缠在胸间的花布条子,扣上两个似空心馒头的物件,心里很惊讶。用手一触,尖挺挺,软乎乎,便溢出几分喜悦。嘴里不由说道:“妈的,这物件,够爽!”转念一想,不对!便追问女人从哪里弄来的。女人不敢露出白丫,说是从南蛮子那儿买来的。男人立刻翻脸,说你让他摸了量了试了。不然这玩艺儿扣在你身上,咋这合适。女人为洗清自己,赶紧把白丫亮出来。男人们既舍不得让自己女人摘掉戴在胸前的玩艺儿,又要显示自己女人的清白,恶状便一咕脑告到白丫父亲二倔头那儿。二倔头将白丫一顿苦揍。白丫起初嘴很硬,说南蛮子是正经的生意人。二倔头听了,豹眼一瞪,呸!哪个正经生意人把大姑娘奶罩小媳妇裤衩挂树梢上卖。从今以后,你在家里呆着吧!
十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南蛮子遣下没有卖出的货品,和白丫同时在小镇上消失了。经过一阵骚动之后,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时隔不久,人们发现小镇西头的长途车站热闹起来。以往不善走动的年轻女人轮番着往城里跑,回来时拎着大包小包直奔自己的屋里。遇上不开眼的男人想翻动,便会挨上女人一巴掌:去!都是娘儿们用的。想看,等晚上。
1998年12月
关于申请建厕的批复
一碗馄饨加两个烧饼吃下去,金局长感到肚子发胀。“噗噗”挤出两个响屁之后他撕下块手纸,急匆匆地奔向厕所。
一推门,坏了!眼前人头一字排开,十个“蹲位”全部占满。见局长破门而入,两个有眼力见儿的“噌”地站起来,屁股都没顾上擦,连声让道:
“局长,请到我这儿来吧!”
“局长,请在我这儿!”
他怎好意思呢。有让吃让喝的,哪有让人家给让茅坑的。虽是局长,也不能图自己一时痛快,叫别人肚里难受呀!金局长迅速摇摇头,从厕所里退出来。在院里转了一圈磨,怎奈腹中之物隐隐作祟,他只好到对门的单位求援去了。
局机关是平房,二百来人的拉尿全得往一个地方挤。五年前,在研究建个厕所的常委会上,还未离休的老局长就提出了“面积大一些,质量高一些,‘蹲位’多一些”的方案。并明确强调男厕所不能少于十个坑,女厕所不能少于五个坑。当时,金局长作为二把手曾提出了异议:一共才几十人的机关,建那么大厕所做何用?干什么也得讲科学,人和坑的配置是有比例的,拉稀跑肚总不能同时吧。
“嗯?”老局长瞟了他一眼,清了清嗓子:“同志们,现在形势发展一日千里,我们的事业越干越大。这干事就需要加人吧?虽是盖厕所的小事,但也得有个长远的考虑呀!总不能隔上几年就盖次厕所吧。再说,讨论研究,上级审批,财政拨款,很不容易嘛!我们何不来个一步到位呢?”
“哎!还是老局长远见卓识呀。”金局长想到这儿,自言自语道。机关由过去的几十人增加到二百多人,弄得厕所人满为患,他早有所察觉。其实,何止是厕所呢?“早晨三处忙,食堂、厕所、锅炉房”,这话都磨破了耳朵。虽是戏言,但怎能说没有牢骚和抱怨呢?本来嘛,别的地方可以谦让等一下,这屎顶屁股门儿的事岂能将就的?
“建厕!”想起早晨捂着肚子转磨那一幕,金局长心坚意定,晚上召开了常委会。会上,他从全方位讲了建厕所的意义,博得一致通过。秘书科将他的讲话加工整理,写成了一份关于建厕问题的书面申请,第二天便呈报上去。
两天之后,建厕申请批转回来。上面一行大字赫然入目。
“申请厕所一事,欠妥。把蹲着坑不拉屎的人请出去,便可化解。”
1993年6月18日
大院遗风
镇机关大院,还是土改时充公的财主私宅。几套阴阳合瓦,连廊四通的宅院串在一起,虽显出质朴典雅,古色古香,但也着实像迷宫一般。县里各委办局都在下面安了“腿儿”,时常来指导工作;乡亲们结婚离婚开个证明,基层的会计报个表册,需在院内几经周折打听,难以一步到位。
可别看不起这套青砖老院,作为基层政权中心,他曾拥有了几十年的辉煌。从建国初期的乡公所到区公委;从人民公社革委会到乡政府,直至后来改称镇政府,牌子隔些年头就换一次。车动铃铛响,往往一块核心牌子一变更,相应机构的牌子也要随之变动, 大院门口墙壁两侧千疮百孔似的钉眼儿,恐怕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小镇经历了十五届政府班子四十一位政府首脑之后,到了第四十二位镇长这儿,似乎要弄出点反响。而反响的代表性则为翻新办公场所,塑造现代意识。
土木之工,岂可擅动。按照程序,要经过镇长办公会研究讨论,达成一致后才能进行运作。
几十年尚未解决的问题,肯定有其难奈的原因,现在想从快从速,也是件难事。镇长办公会议开到第十次的时候,已渐入主题。镇长仍然主持会议,并再次强调了翻新大院的现实意义,然后请与会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主管建筑的副镇长首先发言,他说:“大院翻新,势在必行。现在经济实力逐年增强,各种会议接二连三,老是憋在这鸽子窝样的办公场所,像啥样!财力允许嘛,我们当然要创造优越的工作环境啦。至于工程谁来承接,我看可以给咱们的建筑公司。”
一提起镇里的建筑公司,主管建筑的副镇长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今年的开复工面积到去年同期对比;从工人技术培训到工程建设质量;从提倡职工搞好计划生育到如何孝敬父母。
“我讲几句。”主管建筑的副镇长话音刚落,主管文教的副镇长急不可耐地接上。他是教师出身的知识分子,说出话来引经据典,层次分明:“依我看,大院没有翻新的必要。原因有二:一是机关工作长期属于紧张状态,翻新房屋,要临时搬迁,极大影响工作;二是这几所院子是典型的四合院,造型美观,工艺精湛,很有古老遗风,俱备保存价值,这一点甚为重要。如果可以考虑,还是恪守陈规为好。”
主管文教的镇长呷了口茶,又以古论今,纵横交错,从昌平定陵的发掘到云居寺石经保护;从平安大道铺设时文物意识到老山汉墓的“黄肠题凑”。
发言十分热烈,与会人员开始大体分为两种不同意见,随着讨论的深入,又派生出多种不同意见。当远处传来鸡叫的时候,镇长看看表,做了简单的总结。
“好,大家对大院翻新与否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是好事嘛。我看今天的会议先到这里,啥时再进行讨论,听候通知。”
当第十一次办公会进行的时候,没有等到鸡叫便宣告结束。镇长果断地拍板定案:“关于大院翻新问题,我们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看来意见还难以统一。目前正值年头岁尾,各项工作异常紧张,我看还是把它列入明年计划吧!”
嗟呼!用主管文教副镇长的话讲,镇机关大院的遗风,至少还能保留到明年。
2000年6月3日
野店
艳艳十六岁那年,她爸和她妈见了官司,法庭把艳艳判给了她妈。
娘儿俩无着无落地混了三年,便赶上政策开放。艳艳这时已经中学毕业,出落得越发标致。她妈仗着会做一手好菜,跟她一合计,决定开个小饭店。家里没个主事儿的男人,怕在镇子上和人争不过,便选址在公路旁边的野桑坡。
房子盖好了。她妈找来了那个外号叫尤秀才的小学教员,叫他给起个店名。尤秀才一肚子之乎者也,闲着还爱写个诗填个词什么的。
他矜持了半晌,才摇头晃脑地说道:“贵店坐落野桑坡,远离闹市,动中取静,可谓脱俗。就叫‘野店’如何?即充满情趣,又不失大雅。”
尤秀才一锤定音,又为野店题写了牌匾。完事儿,艳艳妈炒了几个菜。尤秀才喝得脸如重枣,当着艳艳面,一眼一眼地往女掌柜身上扫,说话腔调都有点变味儿。
艳艳影影绰绰地听说过,妈妈做姑娘时,就和尤秀才相好过。只是外婆嫌尤秀才家穷,死活不依,才美梦难圆。艳艳有时想起来挺怨恨外婆,嫁人嫁人,嫁的是人又不是钱。只要人好,豁出去也跟他。
野店虽远离镇子,但旁边这条公路是上京下卫的要道,整天车水马龙。小店因此常常座无虚席。有一拨运煤的车队,三天往返一个来回,东边穿过镇子,西边绕过县城,偏到野店门前停下,说是吃惯了野店的菜味儿。
时间长了,娘儿俩和这帮司机混得熟人似的。有个叫六子的,人长得挺帅,嘴也甜。进了门总是大妈长大妈短的,忙的时候,还帮艳艳跑跑堂儿。挺招艳艳妈待见。可没过多久,艳艳妈看出来了。六子一来,艳艳就脸上放光,脚步迈得也比平时利索。轮到六子吃饭时,艳艳把那菜碟按得鼓尖鼓尖的。艳艳妈心里“咯噔”一下,晚上关了店门,审贼似的问艳艳:
“老实说,你是不是看上了六子?”
“知道还问!”艳艳一肚子不高兴。
“你了解他家情况吗?”“我了解他一人就足够了。”“你可别让他三句好话唬弄了。”“六子不是那种人!”“哼!你爸从前也甜言蜜语,可还不是拿咱像伤风鼻涕给甩了。”“那你当初不嫁给尤秀才?”
说到伤心处,艳艳妈不言语了。憋了好一会,才狠狠地说道:“六子真想娶你,就让他拿一万块钱来!”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艳艳妈被一阵汽车引擎声惊醒。艳艳不见了,床上放着几叠钞票。
尤秀才蹬着小三轮,把艳艳妈的铺盖拉走了。野店至此关门,变得门可罗雀。
村上有人说,尤秀才通晓“周易”,早算出这店成不了气候,所以才冠以“野”字。也有人讲,艳艳和六子在那边拼命攒钱,过不了两年就得回来,这店还得开。到时候,这买卖更得红火。
1993年2月12日
穆乡长养八哥儿
穆乡长从位子上退下来,屁股也就从办公室的座椅移置到自家的沙发上。
穆乡长在位时,遇到同级朋友或部下,总爱把“太累啦”挂在嘴边,再不时地摇几下头,哎一声气,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让人看出他任乡长既绰绰有余,又能日理万机。
退下来的穆乡长也常见到往日的朋友和部下,“太累啦”这句口头禅也只能在他肚子和喉眼之间绕弯打转儿,供他像老牛反刍一样咀嚼与品味。经过一段六神无主的日子之后,“太累啦”的感觉还真令人留恋,那里面闪耀着辉煌,体现着权威,涌动着献媚,表示着服从……而现在,谁还拿自己当做什么,连十岁的小孙子上学前只一句“爷爷我走了”就敢飘然而去。你走了,我说同意了嘛。这要是在乡里……哼!穆乡长越想越添堵。
穆乡长的老伴怕他真“木”了,便从集市上拎回一只八哥儿。
看到这只八哥儿,穆乡长脸上有了笑容,每天几餐精心伺候。讲惯话、作惯指示的嘴巴也得到充分发挥。每当为八哥儿加餐供水时,穆乡长几句说惯的口诀便依序而出:“我不累,没权了。一心一意伺候你,好好学话,别给我丢面子。”
穆乡长从未摆弄过这东西,又只顾心态自然流露,却犯了饲养八哥儿的大忌。
几个月之后的一个节日,新任乡长一行人来到家中慰问。那八哥儿一见这么多人,便在笼里欢欣跳跃。
新任乡长先来个开场白,说:“穆乡长,您劳累了几十年,这回……”
“不累……不累。”话没说完,八哥儿却抢先作答。
“呵!”大伙儿目光直射过去。“没权了,没权了。”那只八哥儿极力显示。一个小伙子走过去拎起笼子惊喜地说:“这鸟要是拿到市上,您要个千八的,遇到买主儿准没二话。”
那八哥儿一听“话”字,紧接下联“丢面子,丢面子。”
穆乡长一脸尴尬地送走客人,一把从笼里掏出八哥儿,眼里直冒火。心里道:“忘恩负义的畜牲,连你也敢嘲笑我,留你何用。”
“叭!”八哥儿被摔在地板上,呜咽几声,便挺直双腿。
1998年3月17日
太阳伞
小镇近河靠水,世世代代的日子也就像这河水一样无息流过。
自从那河上修了橡胶坝,建了度假村,来来往往的人多了,小镇才显得活泛起来。聪明的人便打起商饮服务的主意,想不从土里刨食也能让自己的腰包快速鼓起来,娄子就是其中的一个。
娄子的长相实在不敢恭维,尖嘴猴腮,两只玻璃球儿似的眼珠儿总是滴溜乱转。镇上有的人看过京剧《十五贯》,送他一个绰号娄阿鼠,正好说明他的贼滑精明。
镇上的人干商饮,简单的很。找几根圆木做撐,蒙十几尺蓝布为顶儿,摆几把板凳为座,买卖就算开张了。反正只此几家,别无分号,不吃不喝您就哪儿凉快上哪儿。
娄子贼精,跟别人想的不一样。他托人从城里买来一把五颜六色的太阳伞,两张白色方桌,几把带靠背的塑料椅,往路边一放。嘿!那格调、品味真不一样,远观近瞧,如鹤立鸡群,惹目扎眼。
娄子不弄冷拼,也没热炒,只是预备一些冰镇啤酒、各种饮料和几样小菜儿。用娄子的话说,我定位的客人不是来喂脑袋填肚子的。
太阳伞支起来没几天,生意果然看好。令娄子注意的是,每天傍晚,总有一男一女前来光顾。那男的穿着镇上少见的休闲裤和一件漂亮的T恤衫,透着潇洒。女的大约二十出头,比男的小几岁,穿了一件藕荷色的连衣裙,一头披肩长发,显得高雅。
俩人似乎有一成不变的规律。男的来时,总是从狗四儿的摊上带来一把羊肉串儿,在娄子这儿要一瓶啤酒。女的则让娄子开瓶矿泉水,专要“娃哈哈”牌子的,而且都是各自买单。娄子在报上看过外国人私下聚会,讲究“AA制”,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娄子也说不清楚。
这时候一般也没有外来客,那两个男女坐定,便边喝边聊起来,话题挺广泛,几乎每天一个。那几天电视上正上演《神雕侠侣》,男的就说,李若彤在这部戏中演得最出色,把一个冷峻、善良、美丽的小龙女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女的反对,说就整体而言小龙女的形象不是尽善尽美,她由冷若冰霜到倾心于杨过,显得转的太快、太硬,前后失去人物性格的统一、和谐。这属于演员自我把握程度,也可能出于编剧或导演的水准问题。
娄子懂事儿,知道应该怎样尊重客人,所以从来不向这对男女打听什么。两人来的趟数多了,从闲谈中,娄子仍然听出来了两人的工作单位——就在不远处镇上唯一的那座楼里。
这对男女初来时,娄子心里还有些嫉妒,结账时刀儿下得狠点儿。不过两人从不说什么,要多少给多少,时间一长,娄子反而倒不忍心了。
那对男女闲谈时,娄子就装作擦擦冰柜、抹抹椅子,可耳朵却总支楞着。那两人说出的话,镇上的人没人讲得出。也就是从这对男女的谈话中,娄子知道了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科索沃战争中斡旋所起的作用;知道琼瑶作品中有唯美的成份;知道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产生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到WINDOWS95;知道了地球的最大人口承载量和再生资源等好多没听说过的东西。娄子就打心眼里敬佩这对男女,不觉怨起自己父亲,为什么当初逃学时,只用手打自己的屁股而不用棍子。
夏季要过去的时候,那对男女忽然不再光临娄子的太阳伞下。娄子纳闷儿,就到那座楼里打听,隐约地听到点儿线索:那两人都是大学生,只是男的有了家……
每天少卖一把羊肉串儿,狗四儿也急,就过来问娄子,那对男女咋不来了,娄子说调走了。狗四儿问为啥?娄子说都说人家有那事儿,我他妈就不信,那事儿叫钻狗洞子,能跑到太阳伞下干吗。狗四儿说有没有那事儿你最门儿清,他们每天都说些啥?娄子朝狗四儿一瞪眼睛,说些啥!反正不像你那边客人,一张嘴就操妈日姥姥的。
那对男女不来了,娄子每天老早就拆掉太阳伞,回家闷灯儿蜜。而此时那几个蓝布棚下的客人猜拳行令,正是叫得最欢的时刻。
1998年9 月20日
谎花儿
“谎花儿”,词典上解释为不结果实的花。
小镇上,一提“谎花儿”是谁,知道的人比不知道的人多。“谎花儿”大号叫花海,挺好听的姓为啥让人前边给加个谎字儿?脚下的泡,自个儿走的呗,一看,您准明白。
花海可不是个瞎字不识,一脚踢不出仨响屁的主儿。算起来,花海整整读了十三年的书,还教了一年的书,和一起长大的伙伴比,可谓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了。
十九岁那年,花海参加了高考,几分之差,名落孙山。年迈的父母望子成龙心切,节衣缩食,托了一个在某高校的亲戚相助,让他在那里补习了一年。这期间,花海狂热地爱上了文学,一头扎进古今文学著作的海洋。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写作技巧到现代名家多流派的表现手法;从外国文豪的代表作到滥翻译过来的商品水货,他都一一猎及。特别是对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的作品,更是爱不释手,顶礼膜拜。他立志高考再不能如愿,也要拿起笔,谱写一曲“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牧歌。
他把全部的精力都倾注于文学作品的猎及上,却忘记了到这里的使命。又一次应试后,仍榜上无名,并且考得比上次还糟。
他回来了,踏上他曾蹒跚学步的乡间小路。
回村后的一段日子里,他视自己为骄子,也被乡亲们捧为宠儿。虽没金榜题名,但乡亲们都知道他进过高等学府,拜过讲师、教授,是村上少有的文化人儿。没过一个月,村里都在传播着,东头花家那小子会作诗、写小说哩!为琢磨这门手艺,连考“状元”都扔了 。
当诗人、作家就得有所表现。在田间、地头、河堤、小路,乡亲们几乎随时都可以欣赏到他的“大作”。
堤下承包田里劳动时,他有“蜿蜒大堤尽头处,落叶纷飞百草枯”的旧体诗作;回家的路上,他有“小路啊!你依然如故”的新体诗作。他还经常拿出编辑部给他的退稿信让别人看,因为,稿子虽没有采用,但信上往往也会有几句客气、赞美之词。
渐渐地,乡亲们看不惯他了。庄稼人讲究实在,最忌讳光说不练的把式,他除了能谈托尔斯泰、李白之外,庄稼活儿的功夫一点儿没有。托尔斯泰再伟大,李白的诗篇再千古不朽,那毕竟是一件很遥远的事。如果光用嘴念叨“草死苗活地发暄”就能打下粮食,谁还肯在土地上下那份笨力气。别人开始用讥讽的语言应付他了。花海一听到这些,便恼羞成怒。回到家里,搜刮些“愚昧、蠢笨”的字眼,把他们写进自己的“大作”,以求暂时的快慰。
在家里荒闲了大半年,正好村里小学校补充师资,村干部礼贤下士,推荐他去代课。刚开始,老校长乐得脸上开花,夸他热情奔放,敢说敢干。可没出一个月,他和其他几位老师的关系僵到了白热化程度。不足一年,他留下一张“鄙人才疏学浅,不敢误人子弟”的纸条,扬长而去。
他准备在写作上破釜沉舟,大干一场,整日关在家里,闭门造车,成了真正的“坐家”。他还抄录南宋诗人叶绍翁“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名句,挂在墙上,作为座右铭。
也许春意不浓!也许墙体过高,尽管他呕心沥血,但红杏枝头始终未能露出。正这时,镇里新上马的印刷厂张榜招工,年迈的父母声泪俱下,求他应试,他被说服了。毕竟有高中毕业的实力,成绩居然名列前茅。他被分到排版车间,当了一名排版工。
花海平日里就习惯于呼风唤雨,自命不凡,入场没几天,就感觉鹤立鸡群。接着,他的“作品”在车间不断有所传阅,引起了一些文学知音的崇拜,他更有些飘飘然了。
按说花海早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可在家务农时,却没有一个异性目标。用他的话说:“上帝赋予我一双眼帘,就是为挡住土里刨食的柴禾妞进入视野。”由于他四体不勤,言语刻薄,村里的姑娘们都对他嗤之以鼻。而现在呢?一切都变了,车间里温文尔雅和含情脉脉的少女,时刻在诱发他自我表现的欲望,他的一言一行,都极力显示着与众不同的风范。
工作时间,他不钻研技术,而是拿着出版社送排的稿子品头论足,甚至提笔在定稿上胡批乱改,为此受到车间主任李桐的多次批评。没多久,他发起、组织一个文学社,并着手筹创社刊《潮水》。他毛遂自荐,出任社长兼总编,在全厂排版、印刷、装订各道工序广泛发展会员。他发起文学社的目的何在呢?除了自我表现之外,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读者从他起草的这份“社员守则”中可以得到一点启示。
1、 凡本社社员,要服从社长的绝对领导,不但为繁荣我社创作勤奋笔耕,还要同其它活动保持一致。
2、 凡欲在社刊上发表的文章,思想内容必须符合本社特定阶段的中心任务。
3、 社刊尚处创办初期,缺少经费,每个社员均须积极主动地为社刊编印开动脑筋,竭尽全力。
“守则”实属不论不类,但约束力可谓极大。
花海把社长、总编集于一身,排版车间几个狂热崇拜他的人,也分别被他冠以“副社长”、“副总编”的头衔。文学社一告成立,厂内不少青年申请入社,有的出于热爱文学,有的则是附庸风雅。然而,一个以文学社做招牌,实际上超越了文学范畴的活动在花海的策划下悄然进行。他不甘心做一名职工,他要当车间主任,第一步是以《潮水》做阵地,大造舆论,扩大声势。第二步是发动全车间人员罢工,迫使车间主任李桐下台,然后共同向厂部请愿,拥戴他出任车间主任。
第一期《潮水》很快组稿了。花海以总编身份,逐篇审阅。对不能理解他意图的作者,则反复提示,旁敲侧击。最后定稿十篇,矛头直指李桐。根据“守则”第3条要求,分布在各道工序的社员瞒天过海,借助厂子的设备、工具,使第一期《潮水》迅速出刊。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排版车间几十人突然举行罢工,涌向厂部,要求更换主任,并声称拥护花海领导。李桐是一个红脸汉子,觉得混到这一步,无法再干下去。他不但没对花海谴责和敌视,反而被花海的影响力和组织能力所叹服,竟真诚地向厂领导提出引咎辞职。
事到如今,与其另谋人选,不如顺水推舟。厂部第二天宣布花海的任职决定,排版车间承包的各项经济指标,也转到花海名下。
花海得胜了,他感到自己是个打了天下登上龙廷的皇帝。
工作时间里,他能这样发号施令:“传我的圣旨,车间停产两小时,开个赛诗会。”团支部搞联欢,再三邀请他,他也点头应诺。可联欢会一开始,他拉出车间几十名青工,另立会场,吹拉弹唱一起来,把观众一下子吸引过去,弄得团支书无地自容。他还设立兼职秘书––––一位向他经常目送秋波的少女。
到季度考核时,排版车间的经济指标直线下降,职工的收入也月月锐减,职工们对他失去了信任,并对他逐渐腻味。不久,厂部就以经营不善为由将他免职。他得到的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梦想。
花海陷入了失魂落魄的窘境,只好悄悄地离开厂子。
几亩承包田维持不了一家人的挑费,花海只好再谋生路,现趸现卖,做起商贩。仗着头脑灵活,收入倒也可观。
父母的冷言冷语,哥嫂的白眼儿相待,邻里的嘲讽讥笑,使花海感到元气大伤。他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寂,渴望有人对他理解,给他以慰藉。正在这时,经人介绍,他与邻县的一个姑娘相识了。姑娘有一手娴熟的裁缝技艺,俩人一见面,她就被他侃侃而谈的学识所打动,真诚地爱上他。在花海眼里呢?这个裁缝姑娘虽比不上过去那位秘书小姐标致––––可她在他落魄时,就已飘然而去。正当花海与这位裁缝姑娘定下佳期时,不曾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又一封滚烫的情书飞致花海手中,使他刚平静不久的心情又激起层层涟漪。
情书是和花海曾在同一车间工作过的小兰姑娘写来的。小兰只有18岁,正值天真烂漫的年龄,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她十分敬慕花海的才气。花海和秘书小姐缠绵时,小兰曾一度失望过,在她心目中,花海的形象始终是那样完美。此时,她唯恐再坐失良机,更用火一样的语言向他发出爱的信号。
他也同时接受了小兰的爱,俩人经常幽会在微风习习的晚上。当他把小兰姑娘柔软的身躯拥在怀里的时候,浑身的热血在沸腾,恨不得与未婚妻立刻一刀两断。但静下来,他又不得不考虑,小兰是瞒着父母的,事情一旦公开,她父母不会轻易让女儿找一个年纪比她大八岁,无固定职业并且家境清贫的男人做女婿,弄不好会来个鸡飞蛋打。为了能与小兰保持关系,他只好欺上瞒下,隐去实情。小兰呢?也怕父母干预故秘而不宣。
爱情,给真诚者的是快乐和欣慰,而花海感到的却是惶恐和不安。他脚踩两只船,一面从小兰那里寻求火一般的爱,一面唯唯诺诺应付着未婚妻。小兰和他几次彻夜不归的幽会,终于被她父母察觉,义正辞严地勒令小兰不许和花海继续来往。如果这时俩人情断一方,一场将要到来的风波就会风平浪静。可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缕缕情思,已把他俩死死缠住,频频的幽会依然如故。
小兰父亲经过四处打探,将“他已有恋人,并快要结婚”的消息告诉小兰时,小兰惊呆了!她恨他虚伪,恨他骗去了她的一切,她要报复!没过几天,花海被小兰一个不容怀疑的理由约到家里。刚一进门,小兰一家人便大打出手,小兰也一反往日娇态,在他脸上抓出几条永久的纪念。事毕,小兰父亲又找到他家里,要他拿出五千元的“损失费”。花海干出这等事,一家人都觉得丢尽脸面。他那老实巴脚的父亲怕闹得满城风雨,让未过门的媳妇知道告吹,只得息事宁人。可消息终究不胫而走,五千元“损失费”刚拿走,未婚妻的彩礼就退回来了。
花海绝望了。他准备过一瓶安眠药,想一次吃下去,使自己在梦中悄然离去。他也曾到过河边、树林里游荡,想抬头把自己挂在树杈上或低头扎进河水里,满腔悲壮地告别这个世界。然而,花海终究没有那么做,也许他在进行一种痛苦的反思:自己为什么被别人称作“谎花儿”呢?
1996年3月
|